曾昭旭:我的平凡人生观与生活实践(上)|四海同学会·西山夜话之四
西山夜话 第四期 : 我的平凡人生观与生活实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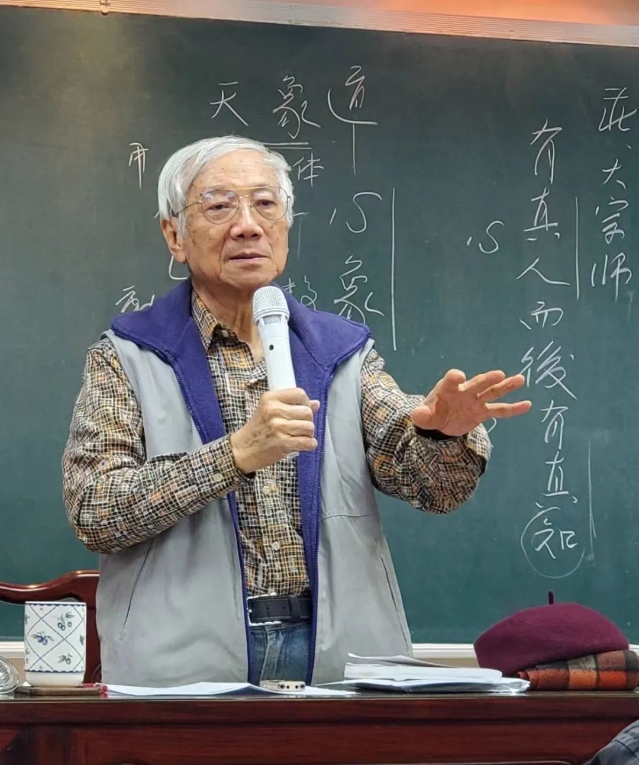
本期讲述者介绍:
曾昭旭: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1941年生,广东省大埔县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专研义理之学。历任髙雄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淡江大学教授、系主任、所长。
曾昭旭先生师从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是港台湾新儒家代表性学者。尤其以爱情哲学闻名两岸,深受青年学子欢迎,曾被著名学者武大哲学院郭齐勇先生赞为爱情哲学教父。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
我的平凡人生观与生活实践(上)
曾昭旭
各位好,我是曾昭旭,谢谢冯院长邀我参与西山夜话,说说我的生命故事。
再过不到一个半月我就满82岁了!我的少年青年的成长故事也许跟当代八零九零后的朋友很不一样,但也许正因如此反而可供参考罢!
今天我主要是提供二十二年前发表的《六十自述》一文(是在一次生命教育研讨会上的演讲,事后整理成文。)请各位指教。但在此应该先作一个引言,交代一下我的为人为学,也许比较有助于大家的阅读和理解。
在当代新儒学的领域中(如近40年前我参与创刊的鹅湖月刊同仁,也被学界称为「鹅湖学派」),我大概是最重生活实践的。在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当代新儒家的大师中,我的为学路数也比较近唐。所以在功夫论、方法论上面,我也特重辩证思维,也就是王船山所谓「两端一致」之说。
——我年轻时读宋明理学诸家之书,每读一家都是初入其门赞叹有加,出其藩篱后又有所不惬。直到读船山书,才全盘熨贴,如有夙契。因此才以「王船山哲学」为题,写成我的博士论文。而两端一致的辩证思维也成为我终身为学为人的路数所在。
当然所谓辩证,绝不止正反合这么简单。所谓两端一致,乃是两端诡谲相即而为一体之意。所以两端互动,并非只在时间轴上进行,而是出入于两端以发现或寻求或创造其相融为一体之道,此道一言以蔽之,即道德生活也。
此所谓两端,最基本而常见的提法当然是形上形下两端(包括智思界现象界两端、体用两端),如道与物(老子)、道与器(易经)、道与言(庄子)等等。
其次是道内在于人而为人之性人之心,于是两端便是指心身、心物、性情、爱欲两端。更衍为愈加错综复杂、幽深曲折的人我两端(人心与我心,而又各有性情爱欲、真假正邪神魔之两可不定),而构成人道德生活的核心课题。
因此,针对人最核心的道德生活课题,我们须对辩证思维重新试作理解(不宜说定义,因这是分析思维的概念)。
首先,与辩证思维相对的当然就是分析思维。但这不宜视之为一对本质矛盾对立的对偶性概念(这正是分析思维的路数),而当视之为有待相即相融为一体的暂分两端(这才是辩证思维的路数)。
那么这是不是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就又构成盾对立的对偶性概念了呢?(依A是A、A不是非A的思想律,是分析思维就不是辩证思维,是辩证思维就不是分析思维。)这不又掉进分析思维的窠臼了吗?
所以我们须厘清:依分析思维,分析思维的确不是辩证思维;但依辩证思维,分析思维其实也在辩证思维之中而与辩证思维似为两端(实只是暂分、姑分)而实属一体。此似二实一之关系即名曰诡谲或吊诡(庄子用语)。
于是我们可以用这诡谲的提法试着去解说一下何谓辩证思维了!
首先就是:所谓辩证思维,乃是先分析,然后取消分析。亦即:在先分析时显分析思维,但在取消时显辩证思维。(当情人在说话时只是在预作铺陈,到关键处不说了,只嫣然一笑,那才是情意与美。)
但以上所说,其实仍只是分析铺陈罢了!到节骨眼时的提法,其实应该是:就在正进行分析活动时,其实已经取消这分析了。这才叫分析与取消分析(非分析)「相即而为一体」,才是正牌的两端一致。
原来不说时的嫣然一笑也是一种说,在认真作抽象的学术思考时也是生命感情的实存。言即行、行即言,两端只是互有隐显而始终是一体(船山的话称为「乾坤并建而捷立」)。
换言之,即使在作最极端的科学分析活动时(极端的价值中立,不涉主观感情),道德心其实也全程都在,只是静默监看而不显。那在什么时候显呢?就是在分析活动完成、告一段落,或走岔之时,道德心就会适时出面叫停(当量子研究结果被政客拿去做成原子弹杀人时,奥本海默的良心就出面了),此之谓「知止而后有定」。
以上就是辩证思维的第一种提法,可以用来充分说明道德生活的内涵与无所不在。而当我们明白分析(科学或价值中立)活动与非分析(道德或价值判断)活动始终是一体亦即关系密切时,(庄子曰: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我们便知两端实相反相成,须分析得更精微,走得更远;当回归道与价值的实存本源时,才能辩证得更周全而圆满。这也才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正途也!(我们亦于此可见老子之不足,即在对「知」不免有忌讳,不敢走太远就怕迷失来时路也。)
现在再谈谈辩证思维的第二种提法,就是「即事说理」。乃因形上之道不可说,形下之物、器与言又以概属有限故,无法指涉无限之道。那我们能怎么办呢?就是将严格的概念语言,巧妙组织成一将概念分界淡化、虚化、混化而融为一整体氛围的存在(老庄即谓之「有物混成」或「浑沌」),遂可无限逼近而指点道了!此混成就道德生活言即可名为事,就文学艺术言即可名为象或意象。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也,亦即所谓「即事说理」,而可意在言外又不离言也。
而综合以上两种提法而构成一辩证思维总模型的,就是大易。阳阴乾坤即暂分之二而实合为易之一体者也。(易系辞云: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六画构成的每一卦,即融阴爻阳爻于其中的整体之象也!故辩证思维也可以称为象思维,亦即非形上之道思维,亦非形下之物思维,乃合二为一之象思维也。
以上概说我的为人为学路数,实即思辩与实践为一的宗旨。在说我的生命故事之前,先点明其中有理,而幸读者之善读也。

下面,就请各位浏览我的《六十自述》:
《六十自述》
——2003年讲于华梵大学「生命教育研讨会」
各位与会同学,早上王镇华老师先提出一个文化理想,近乎是「天道」,所谓「天命」、「天命之谓性」。后来王邦雄老师谈到这样一个理想落到人间,是怎样开展的,天命要动起来向「缘」而运转,这就引进了人的道德创造,也许可以算是接近「地道」。在天地之间需要有人去走,所以我的这场有点象是「人道」,拿我自己生命成长的体验作为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
壹、生命成长总缘自负面的刺激
1、「人之有德慧术知,恒存乎疢疾」
人处于这个世上所遇到的一个基本格局,也就成为人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要说命运与缘,这就是命。当然,人的命千差万别,不过,能促使人成长的命,都不免是遇到负面打击的时候,所以我引了孟子的话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人遇到什么打击,没有关系,那就是我们要恳切面对存在面的一个疾,就在那个地方激发出人的意志力、人的主体性,要把这样的一个生命做一个扭转。
2、幼年的身体健康及青年期的种种病痛
我出生于1942年年初(旧历则是1941年底,属马,所以今年算83岁了),正是抗日战争最炽热的时候,日军已经打到广东了,我母亲带着我和姊姊从广州逃难到家乡——广东的大埔县,因为山地比较没有日本人。我一出生就在逃难,而且逃难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缺乏奶水,又回到乡下,物资非常缺乏,各种的卫生跟现实环境都很差,所以,大概在我两三岁的时候,该生的病都生过了,比如说:麻疹、麻疹后跟着百日咳、又因为病猪死了舍不得丢掉,吃了有毒的猪肉,因此长了一身的皮肤病,还患过疟疾,听说我有三个月没有下过床,几乎死掉。我妈妈奶水不足,所以只能喝米汤,我母亲说,那时候有一罐奶粉便非常宝贝,只能在米汤里头搀一小杓和一和,这样子当然营养不够。
1945年的九月抗战胜利,我母亲就冒险把我带回广州,那个地方医药的资源比较好一点,慢慢可以调养身体。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的身体不能维持两个礼拜是安好的,顶多半个月就会出事,饮食要非常注意,吃一片西瓜就完了,青菜汤一口都不能喝,直到现在,我家的青菜汤一定会放姜,冰棒更不用说,所有冰的东西都不能入口,在广州,有一位医生简直变成我的家庭医师了。我的父亲后来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去钻研中医,后来我就吃父亲的药。在这里,真的让我很早很早就领略到,人之生也,与病俱生。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那我是与病俱生。孟子书中所谓的病其实是疲倦的意思,如「拔苗助长」一章所说,「予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这个病,就是指身体达到健康的平衡点以后往下掉。其实,人病的时间比平衡安好的时间多的多,只是人漠视这个事实,正视生命的脆弱无常,反而很早就不会滥用这个身体,而更早知道身体靠不住,心才靠得住,因为身体基本上属于有限性,心灵才属于无限性。
在1949年底,我跟母亲、姊姊到了香港,我的身体就由两个礼拜可以维持到一个学期,也就是说每个学期都会病一场。一直到1954年,我到了台湾,念小学六年级,然后念中学,大概在青春期吧,中学那六年是一个人的生命力量最旺的时候,所以那六年没有生病。我还记得小学六年级毕业,考完初中联考的那一天,我去买一根冰棒,我要吃一根冰棒,因为已经考完了,不怕病,居然,这次吃了冰棒没有病,我的身体才算有了一个转折。
不过,到了青春期的末期又走下坡了,然后连续的,各种慢性病次第而来。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胃痛,诱因是吃了太多的橘子,管他酸的甜的,都吃。我吃得太多,诱发了十二指肠溃疡。那时我家里经济环境也不好,所以只是忍着,进了师大,才在师大的校医那里拿药吃。但那也只是临时将就,还是常常胃痛。一直熬到大学毕业,到建国中学去教书了,有公保了,看病免费了,才去看我的胃。我遇到一个还不错的老医师,不是热门医师,但是很细心给我试了很多种药,终于试到两种很适合我体质的,然后长期的吃药,吃了两年,十二指肠溃疡才算好了。
但我进入了研究所,很快又发现患了肺结核,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在医生嘱咐不能劳累,要注重身体的情况下写的。在肺病完了之后,陆陆续续也发现眼睛的结膜炎、喉咙啊、痔疮啦等等。我慢慢了解我是一个痨病体质,很容易就失衡;可是,人就是在这么个病中长大,我也渐渐的能够不怕吃药,我父亲开给我的药,再苦我都觉得像喝咖啡,可以品很苦的中药。
在病痛的逼迫之下,我不得不反求诸己,要珍惜这个有限的形躯,比如说:我在患十二指肠溃疡的时候,医生就说有很多禁忌,所有「太」的东西:太冷太冰的、太热的、太酸的、太辣的、太咸的都不能吃;不能吃刚出炉的面包,那会刺激胃酸;不能动激烈情绪,生气、忧伤、兴奋;不应该过度劳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生活行为,要管住自己,这个时候,我曾经给自己订了十条生活戒律,比如:晚上一定要十一点钟睡觉,不能吃「太……」这些东西,不能够动情绪等等,每天晚上检查一遍,凡是有违犯的都在下面用红笔注记。最初的时候都不能认真遵守,每一条下面都是红字,大概过了一个月,才首度出现通通都遵守的情况。所以,持戒是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的一个开端,由戒才能够生定,由定才能够发慧,要先管住自己这个脆弱的形躯生命。又比如说,我在得肺结核的时候,正要写硕士论文,我的硕士论文(《俞曲园学记》)实在是无足称道,唯一可堪告慰的,是写硕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开过一天夜车。说几乎,就是一共只有一天超过晚上十一点睡觉,因为那天写得太高兴,下笔不能自休,其他通通都按部就班。有人说,你看到一个人面有菜色就知道他有作品,写硕士论文,没有人不是弄到后来睡眠不足,赶哪熬啊,我能够在理性的规画之中珍惜自己身体的有限,养成自我控制的习惯,后来我写博士论文(《王船山哲学》)也是很从容,都是固定的,一个礼拜写一章,一章两万多字,一天写五千字四天写完,休息一两天,再找一天整理那些资料,开始第二章,然后两个月写完。这是自我控制的功夫,由于我知道自己糟蹋不起,这是从病痛得到的教训。可以说,我的德行生命的成长,是从这个地方开端,这是我的命,要认命,认命然后才能够立命。
3、童年的逃难经验与穷困生活
除了生理的病痛,就是外在的环境。我一出生就面临到经济环境的困顿。我跟母亲、姊姊到香港,(我父亲则是随着部队到台湾,我父亲是黄埔五期的,当时担任广东潮安县警察局局长),那时候,我母亲非常能够正视现实,很多人带一点钱到香港,只会做寓公,不事生产。我妈妈想着如何维生呢?她想到我们广州家里有一辆缝衣机,她就一个人回去,把那辆缝衣机——不是现在轻巧的,是以前有铁架子的、用脚踩的那种,一个人扛到香港,她没有路条,遇到关卡就一路骂出来;当时局势动荡,居然也就成功闯到香港。就凭着那一辆缝衣机,维持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我母亲到工厂去找工作,那时候我当然失学在家,跟我姊姊,我们一起用缝衣机日夜不停工作,比如缝口袋啊,做球鞋的鞋面啊,甚至还做过编织藤椅啦,绣花啦。做过最多的就是缝毛巾,那个时候毛巾织出来是双幅的,我恢复上学后,跟姊姊放学就先到工厂,扛一大包毛巾,登上两百八十阶,回到山上的贫民区,到家后就剪开,缝个边,第二天早上再把毛巾扛到工厂去还。因为疲倦,常常在昏沈之中把手随毛巾送上缝衣机,缝衣针一下就戳进指甲,断在里面,再拿老虎钳拔出来。我姊姊比较粗心,食指、中指、无名指不晓得戳过多少次,我比较少。
在这样的辛苦当中,我知道人生不是那么轻松,而感受到人生的严肃。我父亲是军人,抗战时官拜上校团长,所以抗战胜利回到广州,有很短暂的优裕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是不爱读书的,功课都叫我爸爸的卫兵、勤务兵帮我做,字不许写得太差,这样分数太少,又不许写得太好,怕老师会认得不是我写的,生活真是浑浑噩噩。要到了香港,才知道人生疾苦,才懂得用功念书,所以,也是由恶劣的环境逼发的,尤其在失学的一年半里面。我后来居然很奇妙的发现,这是我人生非常好的一个阶段:当时七、八岁,也不能做什么,母亲怕我荒废了,规定每天要写一页大字、一篇日记,当然,都是用毛笔写,那个时代还不流行钢笔。我母亲认字不多,也不管我写什么,有写就行,所以我只好胡诌瞎编,我的作文能力就是这么逼出来的。而我那一年半里,既然没事,就去看小说,那时候没有金庸,也没有翻译小说,都是章回小说。我的章回小说十之七八都在那一年半读的,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三国演义》、《粉妆楼》等等。有时候碰到字不认得,不认得也没关系,故事那样的吸引人就往下看啊,看久了以后,字义自然就懂了。我才发现,国文应该这么念,死背是没有用的,得在文章的脉络中去懂得那个字,原来,正是那一年半奠定了我念中文系的基础。我没什么家学,到现在我都觉得失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休学一年也是天赐之福。我们不要把人生抠得那么紧,要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呀!
同时在那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也逐渐懂得「民生」疾苦。失学一年半之后我开始入学了,那时候我唸一所私立小学,学费是每个月缴一次的,缴不出学费,下个月就不要来上课。校长每到月初,就会到每一班去念名字,念到名字的回家,因为还没有缴学费。
这些可以说是我整个人生的转折点——由浑浑噩噩、闹少爷脾气,到认真严肃地面对人生。这是由环境刺激而来的,是这样一个「命」──「命」的狭义就指「命限」,是深深感受到命的有限,才会用自己创造性的心灵去扭转命,否则这个命像各种动物一样,是被设定的,一只猫吃鱼,所有的猫都吃鱼,我们根据一本书了解一只猫,就了解所有猫。如果我们也只是在命定中过了一生,那就是只有命,没有运,更不用说缘,更不用说人生的道德理想,所以后来念到孟子的话都觉得亲切,「人恒过然后能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定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总而言之,要人认真面对人生的有限,牟宗三先生称为「打落到存在面」,「打落到存在面」就是认识生命的有限。
贰、生命成长的必要条件──自由
1、「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存在哲学上总会谈到对偶性的命题,不只逻辑这样,存在上更是这样,所有的存在体验,都是同时发现了人生的有限,也同时发现人生的无限。人的自由与人的不自由,其实是同时被发现的。所以在这个「命」下面呢,一个自由的心灵其实在慢慢的苏醒,慢慢的,有所感有所动,王镇华老师说「苏醒感动」, 「苏」是一种醒过来的初阶,还是朦胧朦胧半睡半醒的,充分的「醒」,当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意外的「缘」来诱发。如果只是一个苦难的人生,可能把人导到另外一个歧途,就是孟子说的;「富岁子弟」固然有他的陷阱叫「多赖」,「凶岁子弟」也有另外一个陷阱叫「多暴」,生存竞争逼使他成为一个很强悍的人,很有生命活力,可是不道德。生存竞争之下,一切的伤人害人都可以被合理化。所以,要从生命的有限性中,导引出人的创造力,人文化成,需要有另外一些机缘,让人在这个命限中对照出另外的一种命,那就不是一个有限性的「命」,而是那个无限性的「天」。「天命」本来是一体连称的,后来把它做一个区分,有限性称为「命」,无限性称为「天」,或者称为「性」。孟子就有这样的区分:耳目口鼻的感官是「性也」,但是「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专把形躯肉身的活动称为「命」,是有限性;至于仁义礼智呢,也是「命」,也是天所赋予的,但是「有性焉」,所以「君子不谓命也」,这个部分专名之为「性」,也就是人的无限性。
2、我的求学生涯与考试经验
自由无限心的由「苏」到「醒」,也有些机缘。我很庆幸到台湾念小学六年级以后,上了建国中学,建国中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学风,就是自由。建中的老师都很性格,从来不点名。我有一位教数学的王文思老师,非常令人敬佩,但是从来不收作业,月考不改考卷,我们的月考成绩单,数学都是空白,只有在期末考的时候,随便给你一个分数。但是,正因为这样子,他没有让我们被引导到升学竞争里面去,他只是认认真真教数学,教我们数学的观念、如何思考。比如:同学问他一个难题,他说:这个题目我也没做过,做不做得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现在做做看,看看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设想有哪几个可能的解决方向。最可能那个,我们先试试。结果此路不通,那么就用第二方案,一个一个试,直到把它解答出来。如果可行的各条路通通试过了,还做不出来,他就会说:「这个题目一定是只能用特殊解法,专门为了这个题目而设的解法,那种解法太特殊了,因此如果各位不会,没有关系,像这种题目不会做,不影响学数学,这一个题目我也不会做。」他平平正正的带领我们走一条思考路,很好,我们很敬仰这位老师,虽然他很懒,从来不改作业。

我们另外有一位音乐老师张世杰,也很性格,一个人单身到台湾来,满怀家国忧思。他有他的热忱,组织当时候非常庞大的中华合唱团,而上课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走进来,他也是不关怀分数,到了学期末,基于学校的义务要打分数,那就打吧,他开始点名,「张三:一表人才,不错。李四:獐头鼠目,六十分。」大家哈哈笑,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大家都认为无所谓,分数算什么?在这种老师的熏陶下,我后来教书也认为升学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教书才是我的事,所以我行我素。
我在大学四年级时在当时的成渊国中试教六个礼拜,结果被我教过的那一班,中间通过一个月考,国文分数就是全年级最后一名,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盯他们重点啊、小考啊。后来我到中山女中,也都是讲我觉得该讲的,同学们说:「老师你讲得实在很好,我们很愿意听,不过,能不能等我们考完联考再讲?」我说不能!因为等你们考完联考,我就没有机会跟你们讲了,我只有现在讲,至于你们考上哪里?关我什么事?考得好不好是你的事。只有这样,教书才会教三十年不厌倦。但,是不是这样子,学生会对我失望不平呢?不是!真的才能感人。我还记得我刚到中山女中教的那一班,只教一个学期,因为他们在寒假的时候把国文老师轰走,临时出缺,我去接。只教一个学期,那班却有二十个人念中文系,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引以为荣。
端正自己的人生的路向,就是忠于自己,这叫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所由,根据我自己来走,以我为准,就是所谓的主体性。
在建中除了有很性格的老师,也有一批好同学。这些同学平常也是骑着脚踏车成群呼啸而过,除了吃晚饭睡觉都不回家,行径看起来跟太保也差不多,不过,我们自问什么坏事都没做,只是发抒我们青春的热力。我们骑脚踏车,也在街上随时跟人飙车、赛车,我也从这边,把我生命里一些蕴藏的能量次第的发抒出来。别看我这样一个人很文弱,我有两次飙车的经验。有一次跟一个同学赛车,他的是新车,我的是老爷车,眼看赛他不过,结果一下子发狠,激发肾上腺素,双腿是自动的狂踩,这样一种意志,终于让那位有新车的同学气馁而放弃不踩了,我就用老爷车赢过他。在这里我发现了人内在意志力的可怕,这也有助于建立我的内在自信。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很自然的,一个青春的生命,各种的芽都能够自由的萌发。再加上我的父母因为是贫贱夫妻,实在忙于生计,无暇去管孩子。在香港,我开始领略到人生疾苦,懂得用功,我的爸爸妈妈就开始对这个儿子非常放心,不过问我的功课。他们不晓得,青春期的生命是非常跌宕的,只要迷上一样东西,其他就可以通通丢掉,迷上数学的时候不管其他,迷上打球的时候不管功课。所以,生命如果不受到外在的干扰、升学的干扰、分数成绩的干扰、父母叮咛的干扰,这个生命就可以在性格的老师、亲爱的朋友间的互动之下,让各种的芽都发出来。
至于成绩呢?我在中学六年的成绩非常跌宕,常常两个学期之间,总平均相差十分以上,也考过前面第二名,也考过倒数第二名,总之迷上什么,就把功课丢掉,等到玩够了,不好意思了,就拣起书来回头念,一念成绩就暴涨十分,就很满意,再把书扔掉,去玩。青春生命应该如此,我是这样子得到我的益处。那成绩单怎么办呢?回家去拿爸妈的章盖一下,我爸妈根本不知道我考几分、念几年级,反正是自我负责。
凭着很重要的,青春期生命的发芽滋长,养成了我比较平均的性格。也许,我的性情先天就是比较平均的,不是专家,不是天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绝对的有决定性,都可以。这样一个平均的发展,倒让我觉得最适合走道德实践之路,也就是说,不作专家就做人吧!说好听叫通人、通才,说得不好听就是周身刀,没一张利,样样精通,也样样稀松。善于调和鼎鼐,人我沟通,就是不能作专家。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人生最大的志气就是做一个人,人最大,比什么都大。
当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到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感到考大学分组是不公平的,你只能选考这一组,不能考其他组,这剥夺了我的机会。因为按照我平均的性情,足以作为我第一志愿的科系横跨各组,包括中文系、艺术系、心理系、植物系、数学系、建筑系。没有法政那一组的系就是了。结果我选择念什么组呢?那时候是为了舍不得那一班好同学,而他们几乎全都是念理工的,我就跟着他们去念甲组、念理工。
当然,在那自由奔放的年代,我文学艺术的才也都发出来。我大概从初二到高三,都在替学校做板报、编校刊。我最虚荣的年代,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建中校刊的主编。那是全省第一本由学生编的校刊,发行到全台湾各中学,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很有名的,圣诞节的时候,会收到各校女生寄来的卡片。
终于,到了高三下学期,学校觉得对我不起,给我特权,准我不用上课,让我自由的安排我的时间。于是,我翻开数学课本,才发现有一本课本是从头到尾都空白,全没上过。我也很自信,每天到中央图书馆去自修,从第一页读起,读完以后信心十足,都懂,预料至少可以考八十几分。结果才考了十三分,却考到师大数学系。你别笑我,那一年的数学方向整个颠倒,所有人都不会做,台大数学系的系状元只考两分,所有考生只有一个人超过六十分,几千人考零分。那是我难忘的经验,有时候我碰到朋友问:我们是不是同年同届?就问你是不是那年考那个数学的?是,那我们就是同一届。结果,我就念了数学系。
进到大学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折。
本来,我所以会念师大数学系,为的是非台大不念。我们高中的那一班很厉害,初中直升高中,一共只有四十几人,十三人保送台大,十八个考上台大,所以我们都是非台大不念。如果考不上台大呢?就去填师大,准备重考比较方便,因为师大是公费,不用缴学费,不必用到家里的钱。
我进了师大以后,一个月,我就觉得重考是非常无聊的事,那个学校没有好学生?为什么还要浪费一年读那种无聊的书,所以,我就放弃重考,要留在师大念。后来又想,既然要念师大,与其做一个数学老师不如做一个国文老师,于是在这里,开始有了对自我人生的规划的一个自觉。我权衡轻重,觉得念数学系是没有前途的,考量起来,念中文系比较有前途,所以,我就决定二年级转到国文系。很多人很惊讶,怎么不念热门系念冷门系?我绝对不是因为数学系念不下去,相反的,大一是我念数学念得最快乐的一年,因为没有升学这些干扰,只是认真学数学,我的微积分,一整个学期每一次考试都是一百分,我成绩最高的另外一门数学课是球面三角与立体几何,学期成绩是九十五分,总而言之,我在数学系的成绩排第二名。结果,我居然不要念数学系。我的考虑是,数学是门纯粹科学,它不能念到大学毕业就算了,它一定要走到数学已知的、已开发的领域的边缘,往未知再踏一步才有意义,也就是必须要进修。但当时台湾只有四个数学系,没有一个研究所,要进修必须出国,而我的环境不适合出国:家里经济环境不好,父母年老,我又没有兄弟,出国摆明是一条坎坷的路。当然我们不应该畏惧坎坷,可那是指当坎坷来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迎上前去,而不是故意选一条坎坷的路去走,因为那样,我们所有的力气都要花在消极的抗争上,和命运抗争,没有余力去做积极的创造,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性情与条件、最顺的路,才能有最多的、积极的创造。比较起来,念中文系要顺当得多了,在国内就可以念到博士,又免费、又可以就近照顾家里的父母,多好呢!当我想清楚了以后,这个决定作下去,就非常坚定。
当时候我数学系的导师大吃一惊,把我叫到家里去,晓以大义,论证我学国文绝对不可能比学数学更有出息,我不为所动。我的英文老师看到我的成绩单(那时候转系要主科老师签字)说:「开玩笑!」叫我拿回去再考虑。下个礼拜我再拿给他,他只好叹一口气签了。只有我国文老师很高兴,赶快就签,因为转到他的系去了。这是我人生中所做的第一个重大的抉择,我觉得人生要为自己做一两次重要的抉择与坚持,才能建立人走自己的路的根本自信。我的第一个重大抉择就是转系,第二个就是悔婚。

再说回来,人的自信,就是在自由的前提下走自己的路。自由是道德实践、道德生活、创造性心灵的发抒的一个消极条件或先决条件。人总要先坚持自由自主,人才可能真的走出自己的路。除了自由意愿的本质,同时要从自由意愿中抒发出一种意志,再从而自然的浮现自我的智慧。所谓「智、仁、勇」──自我肯定是仁,从仁之中涌现出自信、意志是勇,才能够为自己的存在做正确的抉择是智。
在这里,我要顺便谈我的两次考试经验,中间有它的坚持,也有它的智慧。这智慧不是天纵英明的智慧,而是诚实面对人生的必然,自然会出现的智慧。首先就是我考大学,刚才说我们遇到很奇怪的数学题目,那是第二天上午第二节考的,下午还有一堂,甲组就考化学科,很多人考完数学后灰心丧志,觉得完了!所以下午的就放弃。我首先感受到自己的意志──正因为数学考不好,一题都不会,所以更要在下午最后一科把分数扳回来。我在中午那三个小时里,草草吃了两口饭,聚精会神,把两本化学课本从头到尾读一遍,因为化学有很多是需要记忆的,如分子式啦、方程式啦,我印象犹新去考,结果,那一次联考中,分数最高的就是化学和国文,很多人事后懊悔不已,为什么就放弃呢?所以,我学到了人生永远不要放弃。
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悠游自在,读我爱读的书,结果毕业了、教书一年、当兵一年,当然也要考研究所。我过去几年读书是顺自己的性情,觉得很自在,但考试不是这么回事,就有很多无聊的书必须要读,我念着念着就觉得深愧平生之志,为什么为了功利、前途,要这么委屈自己呢?最后我决定,我不考总可以吧!我就放弃不考。那个时候我一个学长,高我一班的易经专家徐芹庭先生,他家在苗栗,听说我不考了,不知是不是专程,跑到台北我家来晓以大义:你这样的人才怎么可以不念研究所呢?我有感于朋友的热忱,只好说:好,我考。但他走了以后我就发愁,怎么办呢?又要忠于自我,又要俯顺流俗。终于我决定,我不能够为了考升学考试而念书,这对不起良心,那么,我得要改一个名义。有时候,行为一样,名义不同就不一样。例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却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义不是客观的教条,仁义就是忠于自己的道德理想,所以我决定,我要藉这个考试的机缘,把我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应该要念的书再念一遍,要无忝于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这时候念书的动机不同,是为念书而念书,就自然念出兴趣来。各位也有过这种经验,平常不念书,到了期中考只好念啊,可是这一念也念进去了,就想有兴趣为什么不早念呢?但现在还有别科要念,就忍痛先把它搁下,去念别科罢!但这样做其实是很糟糕的,因为等到期中考完,你也不会再念了。真有勇气,就管他期中考,既然已经念出兴趣来就继续念,这一科考一百分,其他科当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不念它,只是今天来不及。你敢不敢这么做?我当时就是为了念书,结果念出兴致来,问题被发掘出来了,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本书里没有,只好读别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引申出新的问题,这本书也没有,只好再读一本书,结果一门声韵学我念了十二本书,其中十一本都是不会考的。但这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浪费时间?没有。反正我全念了,管你出什么题目我都会。但纵然如此,还是有些题目你怎么念都不会念到,比如说,那时候有一题每年都会考,四题中的一题,占二十五分,就是出十个反切上下字,叫你说出它是那个声类、那个韵部。很多人都放弃了,我不能丢掉这二十五分,又不能为了考试而念书,那怎么办呢?只好给自己另外一个名义──纯粹为了坚持自己的意志,把它当成纯粹的形式训练:连这样的烦苦你都受不了,还能负担什么责任?所以硬把它念了。意志一振作起来,我居然在一天就把五十一声类每一类有哪些字,两百零六韵每一韵部有哪些字通通背起来。当然,也靠一点我的广东话,用方言区分那些不用背都知道的,用方言无法辨别的部分,就把它编成有意义的句子,牵强附会也方便记忆,当然考完就忘光,反正是形式训练。这两次考试,我一方面激发自己的意志力,同时也没有委屈自我,反而学习到最重要的忠于自我。
这是在「自由」这个前提下所说:包括自我的肯定、忠于自己的意愿、激发自己人格上的意志力,你自然在这地方有了最佳的选择。为了念书而念书,才是对的,不浪费时间,为了考试而念书是白念,尤其,它会引动我们内心的委屈感,那种心理的抗拒,会导致生命的困扰。以上谈的主要就是生命成长的消极条件。
师友反馈
四海同学:非常感谢曾昭旭老师充满智慧与深情的分享!钦佩您为社会幸福的增加探索出一条新路!祝福您的学术成就更好的造福世界!
迎炜: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性情与条件、最顺的路,才能有最多的、积极的创造曾老师阴阳同体,佩服您的爱情哲学。
冯哲:儒家重情,重家,重孝,曾老师的成长故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生命的典范。曾老师提出“诚实是拯救这苦难人生的唯一灵药。”一个诚字,解救一切生命苦难。尤其是夫妇齐家之道。曾老师辛苦了。您拆散自己搭建起来儒家型价值观令人震撼。冬至的西山夜话,喜悦向阳而行。
刘贞麟:曾先生的语言充满智慧,尤其是讲到放下教条的教化而见道,满街都是圣人(心的本来之喜发动,见到了众人的善),到圆融的去应接不同根性的人,(随机应变,阴阳化生之道)。我在绘画创作中也时有感悟,看到先生的分享,更加肯定自己的“受”,也算是间接的印证,非常感谢。祝您身体健康,法雨普洒。
温海明:“这些可以说是我整个人生的转折点——由浑浑噩噩、闹少爷脾气,到认真严肃地面对人生。这是由环境刺激而来的,是这样一个「命」──「命」的狭义就指「命限」,是深深感受到命的有限,才会用自己创造性的心灵去扭转命,否则这个命像各种动物一样,是被设定的。”佩服曾老师的见解,于我心有戚戚焉。
任清君:人生过往,有变革,有故事,有理论,有践行,持续的布施。滋养生生世世的灵魂,用生命照见生命!感谢曾老。后学学习到:空掉曾经搭建的体系,有机会获得新生。所有过往都可成为同理有缘人的资粮。警醒自己,切不可有自以为是可救人之我执我慢。感谢曾老。